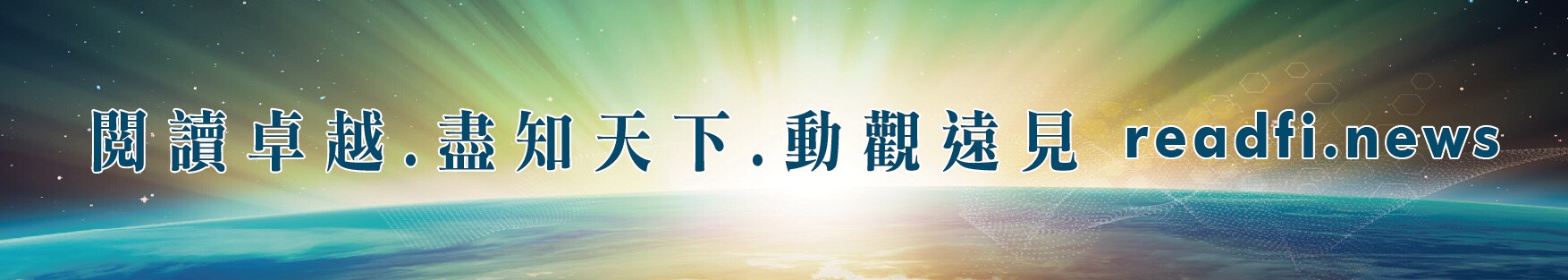需理解中美兩國權力在雙方關係中的敏感性與脆弱性
文/蕭衡鍾

國際關係中的權力是指國際關係行為體對其他行為體實施影響的能力。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由於權力總是指一定行為體對於其他行為體的影響,因此它反映的是一定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而在複合相互依賴視角下理解中美關係,就需要理解中美兩國權力在雙方關係中的敏感性與脆弱性。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某一政策框架內做出反應的程度,即一國變化導致另一國家發生有代價變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價多大?衡量敏感性並非只有跨國界交往規模一個尺度,交往變化所付出的代價對社會和政府的影響也是衡量尺度之一。敏感性相互依賴產生於政策框架內的互動。敏感性假定,政策框架保持不變,而一系列政策保持不變也許反映了在短期內形成新政策的困難,或許反映出對某些國內或國際規則的承諾。」
美中關係的敏感性反應
敏感性相互依賴產生於政策框架內的互動,例如之前的貿易戰是在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主體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內進行的,而美國的一系列徵稅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相對準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
而中國大陸佔世界供應鏈的二十%,生產中斷讓全球供應鏈斷鏈,在貿易戰擴溢與疫情反覆的雙重衝擊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面臨「保四」的挑戰,其中須特別留意金融風險攀升。而國際格局由單極朝向多極化發展,地緣政治衝突加深,美中兩國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衝突中,從貿易戰轉變為全面對抗,包含關稅貿易戰、貨幣金融戰、5G科技戰在內。
川普二次執政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是否持續抬頭、美國是否再次對中國大陸發難引發貿易戰,都引人關注。畢竟挑起貿易戰容易破壞全球多邊自由貿易規則,也很快危及到了世界貿易環境的穩定,也容易引發各國對美國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從決策者個人層面上看,川普政治風格難以準確把握。
但不論如何,美中兩國長期的戰略競爭已成定局,在供應鏈必須分散的布局下,中國大陸作為出口製造業基地的中長期優勢面臨挑戰,海外投資地點的分散代表逐漸降低對中國大陸的倚賴,台灣接單、中國大陸出口的模式正面臨改變,此外,包含RCEP、CPTPP擴大、歐盟推動與東協國家洽簽FTA等,讓區域經濟整合將加速進行,中國大陸擴大東協合作規模、美歐也加大拉攏東協國家,還有東協也在擴大與區域外跨國合作的速度及規模,在川普二次執政後,美中都必須尋求地緣政治經濟關係的新平衡。
美中關係的脆弱性反應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可以定義為「行為體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發生變化之後)強加的代價而遭受損失的程度。脆弱性相互依賴的衡量標準只能是,在一段時間內,行為體為有效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做出調整應付的代價。」是以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今天,各國之間的貿易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別是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在貿易戰面前,沒有贏家,對美中雙方而言,只是傷害多大、程度多深的問題。
從宏觀的經濟資料看,之前美國高盛集團曾預判,如美中貿易戰全面爆發,美國的GDP損失大約為○•四%,中國大陸則在○•二五%左右,而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基於出口資料撰寫的報告也顯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附加值幾乎相當於GDP的三%。這說明,如果與美國爆發貿易衝突,中國大陸受到的損失將更大。
根據美中雙方之前的加稅清單來看,美國主要對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進行制裁,而中國大陸則針對美國的農業。顯然,貿易戰如果全面爆發會使美國農民陷入焦慮,而受限於技術限制出口,中國大陸的高科技行業則會進入一段寒冬期,像是中興此前面臨的困局正是美國在高新技術全球領先和中國大陸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表現。
從消費者個人角度上看,部分商品價格上漲,生活成本提高是兩國民眾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曾表示,美國超過四十一%的服裝、七十二%的鞋類和八十四%的旅遊產品都在中國大陸生產,對這些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相當於對美國人加收一種隱性稅收。
結合美中兩國為解決貿易戰所需承受代價而進行的舉措來看,如果川普二次執政後再次發動貿易戰,美國經濟的脆弱性要小於中國大陸、其承受能力較強,但中國大陸為緩解貿易戰所需承受的代價所做的行動,又似乎比美國更迅速有效。
軍事安全與根本利益的矛盾
美中建交之前甚至建交後的一段時間內,兩國之間都是一種冷戰關係,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思維主導著美中關係的發展,兩國彼此都警惕著對方,軍事實力成為美中關係的焦點。但隨著兩國交流日益密切,依賴程度逐步加深,儘管美中關係走出了「安全困境」,兩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但近幾個月以來,雙方在南海的軍事對峙層出不窮,讓彼此間發生偶發小摩擦的可能性升高。
事實上,美中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且都是有核國家,可以說兩國的和戰走向深深影響著世界政治的走向,在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中、在核武器威懾的恐懼下,美中雙方深知戰爭的嚴重後果;同時,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美中雙方形成了深度的利益交融格局,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機制下,美中之間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成本太過高昂,如果兩國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都將嚴重損害各自的利益。
當然,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對立和美中之間的根本利益矛盾,在一些外交議程上,雙方也會持續存在競爭甚至衝突的情況,特別在台灣議題上,美國諸多「友台」與「挺台」的舉動也引起中國大陸的反彈,視之為挑戰中國大陸的底線。
同時,由於近年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增長與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這個「守成霸權者」對中國大陸此一「崛起挑戰者」的恐懼或威脅感也在與日俱增,印太地區重新成為美國的戰略重心,其不斷強化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強化部署於第一島鏈的軍備建設就是劍指中國大陸的舉動。
由此,戰略競爭狀態下的競爭、對抗與合作在美中兩國外交議程的多個領域中深深交織在一起,隨著兩國依賴程度的加深,美中雙方在研究議題、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都需要將自身與對方的利益得失作為考量的重點之一。
以上言論不代表卓越電子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