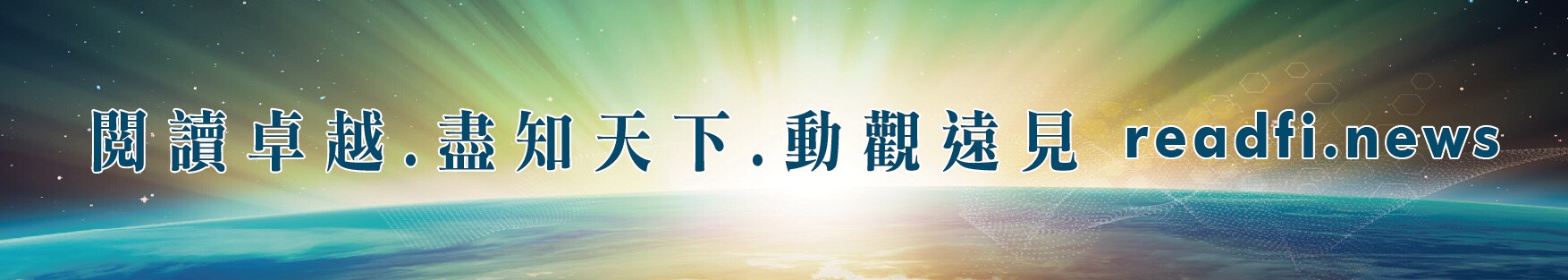從德國總理訪中與中日韓三方峰會剖析美國新圍堵戰略的孤獨與挑戰
經濟合作取代全面對抗 美國新圍堵戰略備受挑戰
Text/Chen Jianwei

在四月份的美、日、菲三方峰會後,美國看似已對中國大陸打造堅不可摧的圍堵陣線,但隨著德國總理蕭茲、俄國總統普丁先後訪華,接著中、日、韓三國又將於五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在南韓首爾舉行中日韓三方峰會,並分別預計由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南韓總統尹錫悅代表出席。美國的新圍堵政策是否將因各國期望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深化而受到挑戰,值得深究。
就在四月中旬,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三人舉辦歷史性的美日菲三方峰會後,美國透過區域軍事同盟所打造的包圍網看似已將中國大陸牢牢包圍,但隨後德國總理蕭茲就率領了國內三個不同政黨的環境、農業、交通等內閣部長,加上德國各大企業界如電機電子大廠西門子、製藥集團默克及拜耳、車廠賓士及 BMW的代表訪問中國大陸。而俄國總統普丁則在五月初前往訪問;中、日、韓三國於五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舉行三方峰會。
從舉足輕重的歐洲大國,再到美國視為堅定夥伴的日韓,這些國家都不約而同選擇在經貿上與美國不同調,持續深化和中國大陸的往來,也對中美間的大國競逐投下許多外部變數。
新圍堵VS遏制 翻譯暗藏中美較勁玄機
圍堵政策(containment)是美國在二戰後與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陣營爆發冷戰(反共主義)時的外交戰略,目的是阻止東南亞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東南亞國家逐步被共產化,依序為中國大陸、北韓、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印度)。當時美國對於圍堵政策的實踐方式就是提供對抗共產主義的國家軍事和經濟援助,也的確有效地限制了共產主義擴張。
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因低廉的勞動力、優惠的投資政策、強大的內需動能及豐厚的土地與自然資源,在短短十數年實現了「大國崛起」,也讓美國漸感威脅,有鑑於此,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開始逐漸轉變,具體方案則第一次由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高級研究員布雷克威爾(Robert D.Blackwill)所提出,聚焦在兩個面向:
一、建立新一輪對美國及其夥伴共同優先及持續受惠的貿易協定,並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就隱含這種模式。
二、透過美國既有的雙邊軍事合作,結合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建立一個管控其軍事科技體制的力量,如由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美國的五眼聯盟(Five Eyes、FVEY),由美國、日本、澳洲、印度所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由澳洲、英國、美國三方組成的安全夥伴(AUKUS),以及由美國與雙邊國家合作並彼此拉攏的軍事合作,再到經濟上由美國、日本、台灣、南韓所組成限制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 or Fab 4),都顯示美國企圖透過所謂「民主盟友」,對中國大陸產生「新圍堵」的戰略。
然而相較台灣廣泛認知的圍堵,中國大陸則更將英文「containment」的理解由「圍堵」轉為「遏制」,「containment」一詞源出於一九四六年時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以X先生為筆名所發表的文章〈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翻譯為蘇聯行為的根源或長電報),當時他認為美國要擊敗蘇聯就得從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型態各層面遏止蘇聯的對外擴張,這也成就了後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歐洲各國儘快從二戰後的經濟蕭條中恢復,讓民眾確信民主世界的國家站在同一陣線,進一步對抗蘇聯持續在歐洲地區的擴張及以經濟的蓬勃發展對比社會主義的經濟沒落,避免共產主義趁虛而入。
那麼「containment」究竟是「圍堵」還是「遏制」?從肯南的理論及後續實踐中不難發現,當時的美國就是在這種戰略架構下,全方位並點對點的在經濟、軍事、外交與意識形態等每個國家發展點上與蘇聯全面對抗,而並非只是地理上的軍事包圍,故「containment」更像是阻止當時蘇聯的各項擴張與發展,與現在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所採取的軍事(串聯雙邊結盟阻止中國大陸軍事擴張)、經濟(中美貿易戰相關技術及人才輸出限制、Chip 4晶片法、新組貿易同盟)來防止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擴張,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大陸與當年的俄羅斯相比,更具有經濟上的影響力,甚至華為竟能突破晶片及技術封鎖令產出5G,都顯示出中國大陸的研發能力已今非昔比,這也是在中美競爭的過程中,美國再度擬串聯各國抵制中國大陸是否有效的最大變數。

歐洲瀰漫戰略自主 中日韓持續加深經濟合作
自歐盟提出戰略自主並成為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主要目標政策後,戰略自主就成為歐盟會議中的重要議程,然而時至今日,歐盟成員國之間仍針對「戰略自主」的內容應該是共識、行為或政策進行探討。最先被接受的看法是進一步的「開放
性戰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OSA)」,其關鍵在於各國先認同了「經濟自主」,各國無不希望加強歐洲的技術和工業基礎、減少關鍵行業中特定外國供應商的集中度(尤其關鍵物料)最後期望將生產鏈拉回或更靠近歐洲。如同馮德萊恩所說目前歐盟追求的應是「降低風險」而非「脫鉤」並期望歐盟成員國之間協調出適當的產業政策。
若從這個觀點切入歐盟的經濟戰略自主,也就不難看出歐洲大國從法國總統馬克宏再到德國總理蕭茲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並不向美國或歐盟般強硬,如此次蕭茲到訪的第一站重慶,除了有許多知名的德國企業,更是串聯中歐鐵路大動脈「渝新歐鐵路」的起點,其終點正是德國第一大港杜伊斯堡港,隨行的交通部長維辛更公開表示反對歐盟如美國般對中國大陸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關稅,亦反對拆除華為5G產品,這也是德國政府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等領域向中國大陸釋出合作的友善信號,並希望積極深化兩國經貿合作。
睽違四年半,令人矚目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也在五月底登場,從會前所釋放的各項訊息到會議內容來看,除延續去年十一月於韓國釜山所舉辦的三國外長會議之共識,聚焦討論經濟、人員交流、數位化合作和氣候、災害合作等領域,而備受外界關心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則輕輕帶過,不變的是中國大陸再次重申反台獨及要求日韓堅守「一個中國原則」。撇開台海因素不論,光是會議議題深度觸及經貿合作,就代表日韓兩國雖然在軍事上與美國有緊密的夥伴關係,但是在經濟上仍不可忽略重要的鄰近大國,且相較於遠程的歐美,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正是日韓想進一步提振出口的重要目標。
政治利益不可凌駕一切 台灣不應恃寵而驕
從上一段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鄰近的日本、韓國,或是過去幾乎都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歐洲國家,除了在軍事上面臨如中東恐怖主義、俄國極權侵略主義等危害世界安全和平的情形時站在同一陣線,在其他經濟、外交事務上逐漸走出自己的路,即便是美國力挺以色列的以巴戰爭,兩國立場在國際上幾乎已被「孤立」,顯示美國正逐漸失去全球的「獨大及唯一性」。
回過頭來,新任總統賴清德打破八年執政魔咒順利接棒並於五月二十日風光上任,然而身兼黨主席的他卻似乎尚未意識到如今的國內、外政治局勢已是丕變,先是在相對少數的立法院以暴力方式抗議在野黨的國會改革法案,挑起朝野極端對立,後又在就職演說中捨棄最基本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引起中國大陸不滿,後者隨後發起為期兩天的「聯合利劍2024A圍台軍演」,此次軍演相較二○二二年更靠近台灣,並呈現包圍態勢,讓賴清德剛起手就充滿危機。
實際上,賴政府真的不可過度依賴美、日等外部勢力,觀察此次就職祝賀團,美國一如往例以AIT主席及處長為主,而備受民進黨期待的日本代表團,也僅由「日華議員懇談會」的議員為主,未見政府官員,且各國仍同步喊出「一個中國原則」,顯見企圖改變現狀並獲得支持恐不切實際,賴政府實不應讓政治利益凌駕於一切,唯有多邊等距、保持理性互動往來,才是台灣未來四年、乃至永久的平安之道。